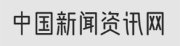一、转型阵痛:数字化转型期智能技术引发教育领域的“科林格里奇困境”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涉及场景众多、关涉主体多样、探索性强、确定性弱的过程性改革,存在由于无法预估技术发展而带来社会风险的可能。以教育智能技术为例,其是在智能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工具和产品,是新兴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与发展的作用结果。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ell)和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通过对人工智能定义的比较分析,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合理地行动、合理地思考、像人一样行动、像人一样思考,这四种类型的人工智能对技术发展的水平逐渐增高。显然,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需要关注其作为工具的“合理地行动、合理地思考”,以及作为合作者的“像人一样行动、像人一样思考”。智能技术于教育而言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给教育带来巨大的推动力、效率和机遇,也能在不知不觉中向教育系统中植入无尽的风险。由于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研究、应用、发展的时间尚短,以及受到技术发展的限制,教育实践主体缺乏智能技术的知识和信息,导致无法在技术应用的初始阶段准确判断技术走势、制定恰当的发展路线,后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负面作用。
我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世界数字化转型洪流的一部分,要求教育系统与新技术深度融合、合理关联。因此随着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深度应用,以及规则滞后和规范缺失,智能技术融入教育发展引发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层出不穷。以技术发展不平衡加剧教育不公平与不均衡为例,从国内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现状来看,互联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发达地区(如一线城市)的公民受到更好的培训、具备更好的信息素养,在资源获取上远优于落后地区(如农村等),资源分配不均衡。此外,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无原则、无规范应用,造成了个体发展产生一系列问题,存在潜在的教育风险,如教师权威丧失风险、算法风险等。从国际层面来看,情况似乎更为严峻,如互联网普及程度存在巨大差异,从美国诞生并向欧洲、中东、拉美地区、亚洲扩散,造成了普及程度“西高东低”以及接入费用“西低东高”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亚非拉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接入宽带,甚至没有制定相关的国家战略规划,这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
数字化转型期的教育发展与技术密切相关,每一个参与教育实践的主体都被技术塑造着、改变着和影响着。与此同时,社会转型期的智能技术引发了一系列的教育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是了解技术风险、设计管理制度、制定规范原则和开展智能技术治理的基础。基于此,本研究以观察和阐释数字化转型期教育主体的实践状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普通公民在技术包裹下面临的困境、混乱、妥协、矛盾与冲突,尝试探讨数字化转型期的教育环境存在何种问题以及怎样如何设计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
二、数字化转型期教育主体的实践状态
(一)困境:技术占有、使用与资源获取存在巨大差距
教育数字化转型期,不同地区的教育主体在技术占有、使用和资源获取上存在巨大的差距。从差距发生的主体来看,这些差距主要存在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不同类型的教育实践主体之间、不同发展程度的学校之间、不同家庭之间。另一方面,个体的经历与感受是大环境作用的细节体现,是数字鸿沟和资源差距这一现实问题在个体身上的具体反映。在硬件占有方面,区域层面的不均衡影响范围最大、结果最为严重。此外,不同家庭的经济状况存在差异,又受到家长认识水平和支持意愿的影响,不同家庭中成长的学生对智能教育资源占有的程度也会不同;学生自身的智能素养也会有所差异,对其在今后的发展中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断加剧技术鸿沟。
在利用智能技术获取资源方面,不同主体的智能素养存在差距,造成其技术的应用能力不同,形成“技术使用鸿沟”,即使是同一主体在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同样面临着随之而来的技术使用鸿沟。需要指出的是,老年人在数字化深度转型的现代社会,正逐渐成为“数字难民”,媒介素养堪忧是导致老年人艰难面对智能化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原因,也是造成技术使用鸿沟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智能时代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毕竟教育的目的是人的发展,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层面都不应当落下任何一个群体。此外,在更为极端的情况下,如在疫情、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下,技术发展不均衡对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更显著。
在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化转型不彻底造成的家庭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公平情况尤为严重。农村儿童仅有的信息获取来源为手机,沉迷于各种短视频和游戏的情况更严重;城市儿童可选择的教育形式较多,即使有一定程度的沉迷,他们信息获取(的多样性)还是可以保证的。此外,不均衡和不平等甚至发生在不同性别之间,但这一情况主要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国家,目前国内在基于智能技术开展的教育上,男女性别之间教育相对公平与均等。女性拥有智能手机的可能性比男性平均低26%,并且这一差异在逐渐扩大,造成性别数字鸿沟的原因主要有资源获得障碍、缺乏教育、固有的性别偏见、社会文化规范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中国不存在性别教育不平等现象,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这一情况依然存在且需要引起重视。数字化转型放大了教育系统中原本就存在的顽疾,需要引起教育改革推动者和实践者的关注。
(二)混乱:主体在虚实融合中穿梭造成其身份认同异化
技术支持下的教育形式多样化是数字化转型期的重要着力点。在线虚拟空间中学习者的表现,其实是现实中“本我”的化身,通过将现实中的情绪、认知不加掩饰地表达,来获得自己在虚拟空间中的身份认同。主体频繁地穿梭在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造成自己的两种应对模式出现混乱,出现主体无意识地放弃模式转化,直接生活在 “真实与虚幻中间地带”的身份认同混乱,最终,虚实融合的教育情境造成教育主体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异化。身份认同的异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责任感缺失。人们利用虚拟身份的隐匿保护,无限地放大自身的个性,层层突破现实责任的束缚,成为一个和真实世界中的自己完全不同的“虚拟人”。长期处于这一状况下的一代人,会产生严重的暴力攻击人格、责任逃避等社会现象。
(三)妥协:家长、教师和管理者开始将权力转让给技术系统
转型期的教育系统与技术系统产生了循环往复的交叠,在“你追我赶”中逐渐控制了身处其中的教育主体。家长、教师和管理者是教育实践中重要的施教主体,分别在不同的教育场景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家长对家庭教育的控制权、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控制权等。虚实融合空间中的身份认同异化通产伴随着施教主体的权力向技术转让,如学校管理者的管理权让渡给管理平台、家长对子女的监督权和教育权让渡给具有交互功能的早教机器人、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权让渡给大数据平台及其背后的算法、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完成学习任务的权利/义务让渡给拍照搜题等“作业神器”。
(四)矛盾:个体成长与思维发展呈现事物发展的两个极端
个体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洪流中浮沉,存在成长过程缺失或方向迷失的风险。最明显的是,技术包裹下的个人成长和思维发展呈现“部分认知过早社会化”与“全面发展无法社会化”两个极端。
首先,学生成长早期阶段呈现社会化严重,表现在儿童接受了太多本属于成人世界的纷繁复杂的信息,而且很多信息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是有害的,这种对超越年龄阶段的某一类信息的过早接触造成了儿童以稚嫩的视角理解他所观察到的成人世界,形成孩子对人性和社会运转规律的认知偏差。
其次,后期阶段呈现社会性缺失,无法实现思维、行为与认知的全面社会化发展。智能技术包裹下的教育实践主体容易丧失社会粘性,进而阻碍个体的全面社会化。在传统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通过分享各自的经验、知识和正在进行的实践,逐渐构建了共同联盟,获得了更多的共同记忆和关注点,这使得成员之间的社会粘性增加。但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信息选择的自由度增大、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机会越少、关注的信息越缺少共同性,人就很容易脱离整个社会的发展、减少不同群体与不同个体之间的经验分享。
同时,智能技术认识与使用不当,造成了教育主体的思维发展呈现“开放”与“收敛”两个极端。其中,过度收敛表现为教育主体的群体极化,即教育主体按照各自关注的“小领域”分化而类聚,在教育群体内部分化出群体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特性。
(五)冲突:正规教育和基于技术的非正规教育之间矛盾与冲突加剧
由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具有公有性、公益性、普及性、公平性等属性特征,是公民获得受教育权的基本保障,如公立学校提供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中心提供的终身教育服务等。由于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具有选拔功能,因此焦虑的家长为了让子女在竞争中保持领先位置,自愿或非自愿地参与了一系列的非正规教育,如校外培训机构、家教服务、课外考试辅导等。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发生在正规教育中,非正规教育也是数字化转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既是一个教育改革过程
教育数字化转型既是一个教育改革过程,也是包含在个体生命中的一段教育旅程。研究采用了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生活在农村-县城-城市不同社会发展区域的祖-父-孙三代人进行观察和访谈,从普通人的视角阐述数字化转型中的教育现实问题。这种“自底向上”的理论建构方式,分析过程细腻且包含细节,能够更好地促进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对话。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或完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智能技术将与教育发展共存,作为智能时代的“局内人”,我们首先要学会向技术要效果,同时也要学会与问题共存、并尝试解决问题。首先需要正视数字化转型期的技术渗透带来的教育风险问题。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融入教育场景、成为教育实践主体的工具和利器,也就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但这一工具对人们造成的影响却呈指数级上升。因此人们需要在正确认识技术风险的同时,提高预测能力、规划能力和适应能力。(通讯员:逯行 黄荣怀)